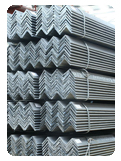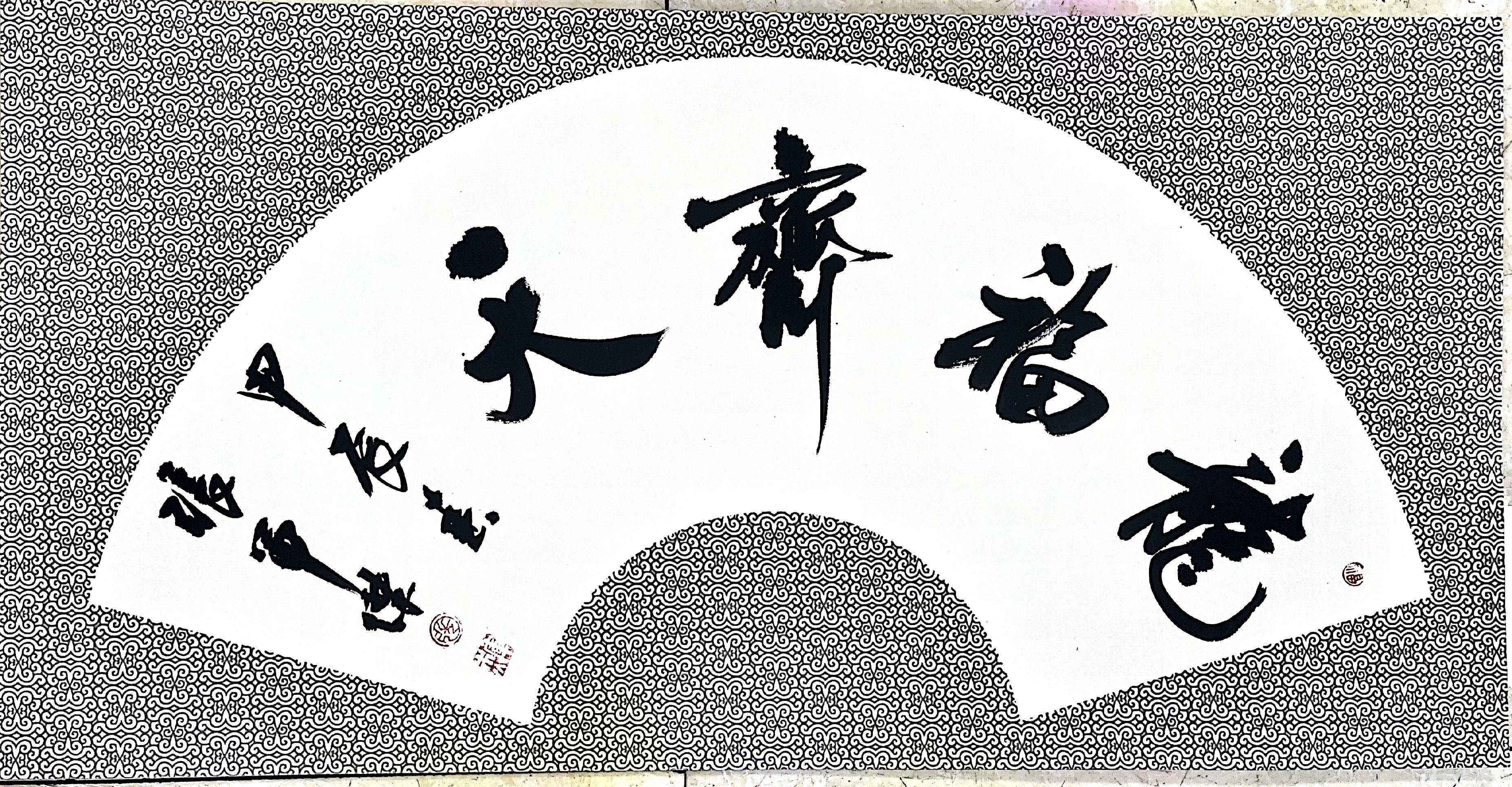滇南風光,春色景邁,山野氣韻,古寨茶香。
在祖國西南邊陲,坐落著一座世界文化遺產——普洱景邁山古茶林文化景觀,它依山而存、緣茶而興、因人而美。
我上景邁山時,正值三月中旬。山下早已是花紅柳綠,山上卻還留著幾分冬日的肅殺。出行的心情總是喜悅的,路途的一棵樹、一朵小花都有很認真的去觀賞。而越往山上,山路盤曲,石階苔滑,偶有幾株早開的野櫻,點綴在蒼翠之間,顯得格外孤清。我想,春大約還未曾到此罷。
山中的春,向來是不知不覺地潛來的。先是幾陣風,吹得林梢微動;繼而幾場雨,潤得泥土微濕。待人們發覺時,那春意早已爬滿了枝頭,鋪遍了山野。
行至半山腰,忽見一株老梅,橫斜出水,花開正盛。那花白中透紅,紅里泛白,如雪里燃著幾點火苗。樹下立著個老翁,青白臉色,皺紋間時常夾些風霜的痕跡。他見我駐足,便道:“這梅樹已活了百余年,年年開花,從不失信。”
我問他山中春事,他搖頭:“還早哩。這梅花不過是報個信,真正的春,還得等上十天半月”。果然,再往上行,樹木愈發稀疏,偶有鳥雀飛過,也是匆匆,不肯停留。山風掠過耳畔,猶帶寒意。我不免有些失望,心想此番怕是遇不見山中的春了。
在山中住了兩日。第三日清晨,推窗一看,不由得吃了一驚——昨日還枯槁的枝椏,今日竟抽出嫩芽來了!那芽尖微微泛紅,如嬰兒的手指,怯生生地探向天空。遠處的山巒,也仿佛一夜之間披上了輕紗,朦朦朧朧的綠,由近及遠,漸次暈染開去。
我急步出門,循著小徑走去。但見道旁的野草,不知何時已鉆出地面,嫩綠的葉尖上還頂著露珠,在朝陽下閃閃發亮。山澗里的水也活泛起來,叮叮咚咚地唱著,偶爾還夾著幾聲鳥鳴,清脆悅耳。
轉過一道山梁,眼前豁然開朗。一片茶園展現在眼前,茶樹排列整齊,新葉初綻,綠得發亮。幾個采茶女穿梭其間,手指翻飛如蝶,不時傳來陣陣笑語。她們身著靛藍布衣,頭戴竹笠,在綠海中時隱時現,宛如一幅活了的圖畫。我走近一株茶樹細看,那新生的葉片不過指甲蓋大小,邊緣還微微卷曲,葉脈清晰可見,摸上去柔軟如綢。摘一片含在口中,先是微苦,繼而回甘,竟有山野的清氣。
一位中年茶農見我新奇,便說道:“這是頭春茶,吸足了冬天的養分,又得了春天的雨露,自然好喝。”說著,他指向遠處的山峰:“你看那云霧,像不像龍在游動?我們這兒有句老話:云霧繞山三日雨,春茶發芽七分甜。”我回頭望向他,只見他黝黑的臉上刻滿皺紋,眼睛卻明亮有神。“很好,清甜得很。”我答道。
正說話間,一陣山風吹來,帶著泥土和草木的芬芳。我忽然明白,春不是突然降臨的,它是一點一點滲透進來的——從土壤的松動,從樹液的流動,從花苞的膨脹,從鳥獸的躁動。它悄無聲息地改變著一切,待到人們察覺時,早已是春深似海了。
春天終究是公平的,不論高山平地,遲早都會抵達。只是山中的春,來得矜持,走得從容,不似平原地帶那般喧囂張揚。它像一位含蓄的隱士,將滿腔熱情藏在冷靜的外表之下,唯有細心之人,方能窺見其真意。人生何嘗不是如此?許多美好的事物,往往就在我們身邊悄然發生,只是我們太過匆忙,未曾留意罷了。
傍晚,我坐在茶祖廟旁的石階上等一場日落。夕陽將古茶林染成金色,傣族祭壇在余暉中若隱若現,宛如“山林精靈的秘臺”。遠處廣場上,村民跳起民族舞,歌聲與牛鈴交織,群山成了最忠實的聽眾。
次日離開時,山風送來一縷茶香。回望景邁,云海仍在翻涌,古茶林靜默如謎。這里的美,不止于視覺的盛宴,更在于人與自然的默契,景邁山的故事,是茶的故事,更是生命與時光的故事。(韓城公司 張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