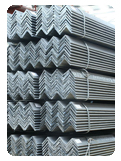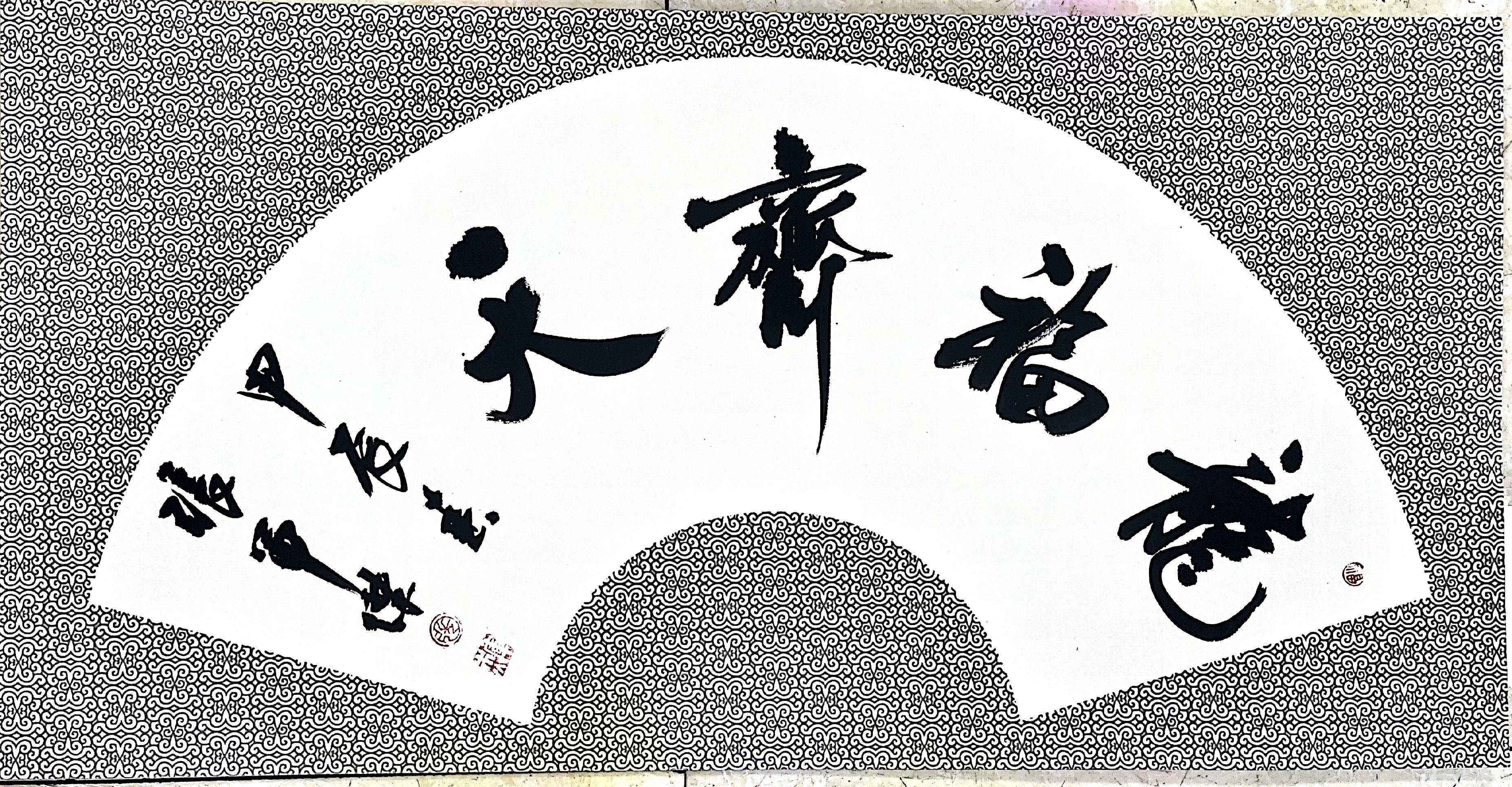清明雨絲裹著青草氣息,輕輕落在老宅外的麥田里。我握著那根斑駁的竹拐杖,站在爺爺的墓前。這拐杖曾是他失明后的眼睛,竹節(jié)上深淺不一的裂痕,像刻著時光的密碼,輕輕摩挲,往事便如渭河的波紋般層層漾開。
爺爺生于亂世,幼時家中青瓦連檐,家境殷實。太爺爺常將米糧分給饑民,冬日里給長工們縫制棉衣。那時的竹杖還是太爺爺手中把玩的雕花物件,綴著玉墜,象征家族的體面。后來時代的洪流裹挾著變故,家產散盡,太爺爺留下的竹杖成了爺爺沉默的支點。
動亂年代,平原上的匪患如蝗蟲過境。奶奶被擄走那夜,爺爺拄著竹杖追出三十里,杖尖在麥茬地里劃出凌亂的溝壑。土匪將奶奶綁在草垛上逼問家財下落,爺爺嘶吼著撲向火堆,竹杖在混戰(zhàn)中折斷半截,煙塵嗆瞎了他的雙眼。奶奶化作焦土,爺爺卻攥著殘杖跌跌撞撞回家,從此那根竹杖再未離身,它成了他丈量世界的尺,也成了拴住七個兒女的繩。
失明后的爺爺用竹杖探路,在公社的曬谷場篩麥粒換糧。竹杖敲擊木锨的節(jié)奏,是父親和伯伯們童年最熟悉的搖籃曲。三年饑荒時,他拄著竹杖摸黑走遍十里八鄉(xiāng),用最后半袋紅薯從糧站換來一捧麩皮,熬成糊分給七個孩子。姑姑們總說:“爹的竹杖一響,灶膛就有火星。”
我是孫輩中最小的一個。每逢清明,爺爺總用竹杖輕敲我的腦袋:“莫踩麥苗。”他眼睛渾濁如老井,卻能憑風聲辨出是我偷吃了供桌上的麻花。姑姑們帶來的米花糖、核桃酥,他用竹杖勾下房梁上的竹籃,悉數塞進我懷里。飯桌上,他摸索著撿起掉落的饃渣,喉頭滾動著嘆息:“糟蹋糧食,要遭雷劈的。”竹杖就倚在條凳邊,像位嚴厲的監(jiān)工。
如今的竹杖已裹滿包漿,杖頭嵌著爺爺用麻繩纏補的裂痕。父親說,這是太爺爺栽在祖墳旁的金竹所制,根系連著渭河的水脈。每年清明,我代替爺爺拄著它穿過油菜花田祭掃。平原的風掠過麥浪,竹杖點地的聲響與二十年前重合,那時爺爺牽著我的手,杖尖撥開田埂的荊棘,講述太爺爺如何在時代的風雨中護住祠堂牌位。
墳前新麥又綠,我學著爺爺當年的模樣,用竹杖挑起紙錢,看灰燼盤旋如黑蝶。七個孫輩中,唯我繼承了這根竹杖。三叔曾提議換成紅木雕花的,卻被父親喝止:“竹子里住著爹的魂。”是的,這斑駁的竹杖里藏著地主少爺的傲骨、失明父親的隱忍,還有在饑荒與動蕩中始終挺直的脊梁。
夕陽把竹杖的影子拉得很長,恍若爺爺佝僂的背。我忽然懂得:這根穿越百年煙塵的竹杖,早不是尋常物件。它是家族的血脈在苦難中擰成的繩結,是清明雨里永不熄滅的燭火,更是爺爺留給我們的,最沉默的遺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