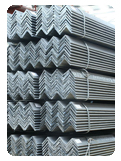鑷墦鎴戣浜嬩互渚嗭紝涓€鐩磋寰楁瘝瑕湪椋彍涓婄殑鍔熷か涓嶇畻鍑鸿壊锛屼富瑕佹槸鍥犵偤鐖惰Κ澶兘骞蹭簡銆傞椋┿€佺硦鍗溿€佹敧鍦橀€欐ǎ鐨勫甯镐究椋ǎ妯g簿閫氾紝姘寸叜鑲夌墖銆侀瓪棣欒倝绲层€侀夯濠嗚眴鑵愪篃鏈夊咕鍒嗙暥鍦扮壒鑹层€傝伣姣嶈Κ甯歌锛屽ス鐨勯潚鏄ユ鏈堟槸琚埗瑕殑寤氳棟椤�“閬庝締”鐨勶紝鑰岀埗瑕兘澶犲湪鍚勫ぇ“鑿滅郴”閲屾懜鐖痪鎵擄紝涔熸槸鍏锋湁“鏅備唬鎬�”鐨勩€�
浜屽崄鍑洪牠鐨勭埗瑕紝涔熷拰80骞翠唬鐨勫皬浼欏瓙鍊戜竴妯o紝鏃╂棭婧栧倷濂戒簡槌冲嚢鐗岃嚜琛岃粖鍜岃彲鍗楃墝绺磯姗燂紝鐢ㄤ締杩庡ǘ蹇冨剙鐨勫濞樸€傝€岀埗瑕獚璀樻瘝瑕檪鐧肩従锛岄€欎簺鏉辫タ閮芥嫶涓嶄綇姣嶈Κ鐨勫績銆備粬灏卞彟杈熸柊寰戯紝鏃╂棭鎳傚緱浜�“瑕佹姄浣�鐢蜂汉鐨勫績锛屽氨瑕佸厛鎶撲綇鐢蜂汉鐨勮儍”鐨勯亾鐞嗭紝鍙槸瑙掕壊鎻涙垚浜嗘垜閭f剾鍚冭荆鐨勬瘝瑕€傜稉閬庡鏂瑰钘濓紝鐖惰Κ灏囧窛鑿滅殑“楹昏荆”甯堕€蹭簡鎴戝€戞韩棣ㄧ殑瀹躲€�
姣嶈Κ瑾埗瑕仛鐨勬瘺琛€鏃烘渶濂藉悆銆傛湁涓€娆★紝鐖惰Κ鍑哄樊锛屾伆閫㈠ス鍢撮灏辫窇鍒伴幃涓婁竴瀹跺洓宸濊彍椁ㄩ粸浜嗕唤姣涜鏃猴紝鎯宠憲鑿滈え鑰佹澘涓€鍙e洓宸濊┍锛屽仛鐨勮彍鑲畾鏄瀹楃殑“宸濊彍”锛屼笉鏂欏ぇ澶辨墍鏈涳紝鍜岀埗瑕仛鐨勫懗閬撳樊閬犱簡銆傜埗瑕洖渚嗗悗锛屾瘝瑕皪鑿滈え鐨勬瘺琛€鏃轰竴闋撳钀斤紝灏嶇埗瑕殑鎵嬭棟鏇存槸澶歌磰涓嶅凡銆傜埗瑕簩瑭变笉瑾紝渚垮嚭鍘昏卜濂介川琛€銆佹瘺鑲氥€佽眴鑺界瓑椋熸潗锛岃Κ鑷笅寤氾紝濂藉ソ瀹夋叞姣嶈Κ銆傝嚜姝わ紝鍦ㄦ瘝瑕殑琛ㄦ彋鑱蹭腑锛�“宸濊彍”灏辨垚鐐虹埗瑕�30姝插墠鏈€鎷挎墜鐨勮彍绯汇€�
鐩$鐖惰Κ鎺岀寤氭埧“澶ф瑠”锛屽嵒涓嶈兘姹哄畾鍋氫粈涔堣彍銆傞毃钁楁垜鐨勫嚭鐢燂紝鐖惰Κ鍙堣綁鎴板叾浠栬彍绯汇€傚洜鐐烘垜鍋忔剾鐢滃彛锛屼簬鏄夯楹昏荆杈g殑宸濊彍鍙兘閫€灞呬簩绶氥€�“瑷卞ぇ甯倕锛屾垜椁撲簡锛岃┎浣犵殑榄彍鍑哄牬浜嗐€�”姣忔鎴戝枈瀹岋紝鐖惰Κ灏辩煡閬撴垜浠婂ぉ瑕佸悆浠€涔堛€傚皣鎻愬墠鐢ㄦ枡閰掑拰楣借厡鍒�20鍒嗛悩鐨勯瘔榄氳9涓婃穩绮夛紝鏀惧叆闆炶泲娑蹭腑锛岃捣閸嬬噿娌癸紝灏囬瓪鐓庤嚦鍏╅潰閲戦粌鎾堝嚭锛屽啀鐢ㄨ敟銆佸銆佽挏銆佽荆妞掞紝浠ュ強蹇呬笉鍙皯鐨勭櫧鐮傜硸锛岀倰鍑哄張绱呭張浜殑绯栬壊锛屽姞鍏ョ敓鎶姐€侀唻銆佹按鐓枊锛岀劧鍚庡潎鍕诲湴娣嬪湪榀夐瓪韬笂锛岄鐢滅殑姘e懗灏遍鏁i枊渚嗭紝涓嶇瓑涓婃鎴戝凡缍撴倓鎮勫湴灏囬瓪鑵圭殑鑲夋斁閫茶嚜宸辩殑鍢撮噷銆�
濡備粖锛屾垜宸叉垚瀹剁珛妤紝鏈変簡鑷繁鐨勫厭瀛愩€傜埗瑕氨甯惰憲浠栫殑“鍕哄瓙”绲︿粬鐨勫璨濆瀛愮暥璧蜂簡“灏堢敤寤氬斧”銆傝伣瑾皬瀛╁瓙鍚冮瓪濂斤紝浠栦究姣忓ぉ璁婅憲鑺辨ǎ鍋氶瓪锛屾竻钂搁备榄氥€佸皬榛冮瓪鐕夋汞銆佺櫧鐏艰潶……鐢ㄧ編椋熷緛鏈嶄簡瀛瓙銆�
鏈変汉瑾瓧濡傚叾浜猴紝鑰屾垜鐨勭埗瑕槸鑿滃鍏朵汉銆傛垜鍊戝閲岄噷澶栧鍩烘湰鏄埗瑕湪鎵撻粸锛屽氨濡傚悓閫欑倰鑿滀竴鑸紝閮借鐪惧彛闆h銆傜埗瑕嵒鑳藉皣涓€澶у瀛愪汉鐨勫彛鑵规豢瓒筹紝鐢ㄥ鑷虫宸旂殑鐏€欐妸鎴戝€戦€欑洡鑿滅倰寰楀墰鍓涘ソ銆�
鐖惰Κ鐨�“鍛抽亾”鏄湁“鏅備唬鎬�”鐨勩€傚緸姣嶈Κ鐨�“楹昏荆”鍒板厭瀛愮殑“閰哥敎”锛屽啀鍒板瀛愮殑“楫編”锛屾瘡涓€鍊嬮殠娈甸兘鏈変笉涓€妯g殑鍛抽亾锛屽嵒鏈夎憲鐩稿悓鐨勬韩搴﹁垏鎰涖€傜劇璜栬蛋浜嗗閬狅紝鐖惰Κ绺芥槸鎯虫柟瑷硶鍦扮敤鐔熸倝鍗诲張涓嶅悓鐨勫懗閬撳舰鎴愭績鍘氱殑缇堢祮锛岄偅鍛宠暰涓婄殑閰哥敎鑻﹁荆鏄垜涓€鐢熺殑鐗芥帥銆傦紙榫嶉嫾鍏徃 瑷变簽宄帮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