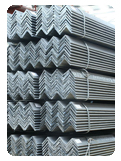我的家鄉(xiāng)在物華天寶、物產(chǎn)豐富的關(guān)中道,每年隨著布谷的叫聲劃過湛藍(lán)的天空,一陣陣暖風(fēng)散開了麥子的渾身毛孔,沉甸甸的麥穗,就天見天的改變著自己的膚色,青澀的綠意褪去,健康的小麥色爬上鄉(xiāng)親們的臉龐。
童年的記憶里,我從老爸的磨鐮聲中睜開眼睛,老媽早已經(jīng)熬好了清涼解暑的綠豆稀飯,晾在院子里的石板桌上,我懵懵懂懂地抬頭望了望天空,啟明星锃亮,晨風(fēng)越過低矮的土墻,送來麥子成熟的味道。這時(shí)候,老爸對(duì)著磨好的鐮刀吹一口氣,側(cè)耳聽聽,滿意地在褂子上擦了兩下,仰起脖子咕咚咚一大碗綠豆稀飯下肚,拉起架子車,一把就把我放在車轅頭,大喊一聲走了,迎著太陽,去西坡開鐮,拉開了夏收的大幕。
麥香把整個(gè)麥田淹沒了,太陽炙烤著老爸的脊背,褂子上已經(jīng)布滿了汗?jié)n,一眼望不到頭的麥浪中,老爸的鐮刀聲是主旋律,他最大限度地彎下腰去,鐮刀迅速地“親吻”著已經(jīng)酥軟的麥稈,左腿攬著割下的麥子,右腿順勢(shì)一提,鐮刀又一次割了過去,這樣重復(fù)三幾下,一大堆麥子整整齊齊地躺在老媽挽好的“麥繞”上,老媽單膝一壓一轉(zhuǎn)一壓,左右手麻利地交叉,一大捆麥子緊緊地?fù)肀г谝黄穑S著老媽的起身,麥捆變戲法一樣立了起來,沐浴著正午的驕陽,像秦始皇兵馬俑,威嚴(yán)地站成一排排。我提著水罐,深一腳淺一腳地跟在爸媽后邊,撲著上下翻飛的蝴蝶,攆著突然竄出的野兔,太陽也把我幼稚的臉龐曬成了小麥的顏色。老爸終于直起身來,長長地舒一口氣,大口喝水,老爸驕傲地檢閱著身后部隊(duì),大聲吆喝一下,又把自己俯身于麥浪之中,收獲著自己莫大的喜悅,以及這個(gè)家的美好未來。
麥場(chǎng)上,把原來頭尾對(duì)齊的麥捆分散、搞亂,均勻地?cái)傇邴湀?chǎng)上,驕陽高照,麥子上像下了火一樣,顏色變得干黃。老爸搖身一變,一改割麥時(shí)的厚重,身手敏捷地跳上手扶拖拉機(jī),啟動(dòng)掛擋加油減油,突突突,順時(shí)針橢圓圈,從最外圈碾起,就在這轉(zhuǎn)圈間,麥粒與麥殼開始分離,轉(zhuǎn)時(shí)要一邊收一邊放,要照顧到每一處麥子都能被碾到。碾得差不多時(shí),老爸一聲吆喝,大大小小一家七口人,手持木杈開始“翻場(chǎng)”,即把已經(jīng)壓平的麥稈翻過來繼續(xù)碾。這樣反復(fù)折騰三四遍,麥粒脫下來了,麥草也碾好了。開始“起場(chǎng)”,把麥子挑起來使勁抖,讓麥粒從麥草中流出。把麥草收集成堆,剩下厚厚一層裹在麥衣里的麥粒,用“擁板”的推成堆,這個(gè)環(huán)節(jié)是小孩子們的“戰(zhàn)場(chǎng)”,你擠我我擠你,鬧成一團(tuán),歡聲笑語渲染了整個(gè)麥場(chǎng)。起場(chǎng)后就該是“揚(yáng)場(chǎng)”,就是要把麥粒和麥衣分離開來。“揚(yáng)場(chǎng)”是借助自然風(fēng)力來進(jìn)行,老爸看中風(fēng)向,一木锨麥子麥殼混合物迎風(fēng)而起,麥子落在近處,麥殼落在下風(fēng)向,老媽嫻熟地配合著掃去麥粒上的雜物。就這樣你來我往,麥子在麥場(chǎng)的中央堆成一溜,像一只豐腴的魚。此時(shí)西山銜著夕陽,五彩繽紛。老爸安靜地坐下來,看著眼前的麥堆,悠閑地抽起煙來,他變戲法一樣,用麥稈編制成了一個(gè)籠子,把螞蚱裝在里邊,我趴在老爸的結(jié)實(shí)的腿上,聽著螞蚱的歡唱,進(jìn)入了有關(guān)麥子的夢(mèng)鄉(xiāng)。
金黃的月亮升起,天地間有短暫的靜默,老爸憧憬著顆粒歸倉,上好的擱在樓上麥包里攢起來,有了那幾十擔(dān)的麥子,老爸的心里才踏實(shí)。也是因?yàn)橛辛他溩樱膬号畟儾拍艹缘蔑柎┑门覃溩右粯樱荒昴隉o憂無慮地生長。吃了麥子做成的面條饅頭,麥子就流淌在我的血液里了。
盡管我已經(jīng)離開生長麥子的土地三十多年,但是麥子依舊高高在上,領(lǐng)著我走過無邊無際的黑夜白天,我永遠(yuǎn)走不出麥子的影子,麥子就是我生命的輪回。風(fēng)吹衣袂,布谷聲切。我分明觸摸到了麥芒的尖銳,只是原先鋒利無比的割麥鐮依然安靜地掛在老房的檐下,已經(jīng)銹跡斑斑。老爸已經(jīng)長眠于他耕作了一輩子的麥田里,但是我深深的知道,關(guān)于麥子的記憶,在一代代人的胃里,一代代人的心里,熠熠生輝。(金屬科技公司 王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