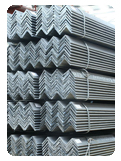晨霧未散,高爐的煙囪先醒了。二號(hào)高爐像位披著銀甲的巨人,把第一縷白霧呵成裊裊的云。初春的鋼城依然籠罩在一層薄薄的寒意中,但空氣中已經(jīng)能嗅到一絲不易察覺(jué)的暖意。透過(guò)天空中那懸浮著淡青色的霧靄,我看到第一縷陽(yáng)光灑向這片鋼鐵之城。
道口鐵軌旁的蒲公英總是最先知曉春信,煙囪的喘息尚未被陽(yáng)光捂暖,它們便從枕木縫里鉆出來(lái),頂著薄霜舒展絨毛,金黃的小太陽(yáng)在石頭堆上搖搖晃晃。我總疑心這些倔強(qiáng)的花兒是去年鐵水罐濺出來(lái)的火星變的,要不怎么能在鐵銹色的土壤里活得這般恣意?還有那枕木縫里鉆出幾簇紫花地丁,倔強(qiáng)地仰著臉,吮吸著從冷卻塔飄來(lái)的溫?zé)犰F氣。美麗花大道旁的柳樹(shù)開(kāi)始抽芽了,嫩綠的新葉從褐色的枝條間鉆出來(lái),怯生生地打量著這個(gè)世界。你看那積攢了一冬運(yùn)勢(shì)的紅葉李,粉嫩的花骨朵一個(gè)接一個(gè)的爬滿了樹(shù)枝,就等著一個(gè)大太陽(yáng)的好天氣,盡情綻放。煉鋼廠西南角的圍墻根兒也熱鬧起來(lái),爬山虎的新芽像誰(shuí)拋出的綠絲線,在紅磚墻上歪歪扭扭織補(bǔ)時(shí)光,那些蜷曲的觸須在紅磚墻縫里游走,倔強(qiáng)地繞過(guò)“安全生產(chǎn)”的褪色標(biāo)語(yǔ)。蒸汽管道突然發(fā)出低沉的震顫,驚得麻雀從冷凝塔頂部的鐵梯扶手上四散飛起,翅尖掠過(guò)煙囪口裊裊升起的白煙。工人們匆匆走過(guò),很少有人注意到這些細(xì)微的變化。但我知道,它們正以它們的方式,訴說(shuō)著春天的到來(lái)。
突然間傳來(lái)了震耳欲聾的鳴笛聲,順著聲音的方向我看到,原來(lái)是載滿鐵水的火車正在緩慢駛過(guò),而鐵軌縫隙里冒出的野莧菜,紫紅色莖葉正在輪軸的震顫中輕輕搖晃。這時(shí)轉(zhuǎn)爐出鋼的聲音響徹廠區(qū),金紅鋼水奔涌的剎那,東邊朝霞正將云絮染作熔融的琥珀色。龍門吊的探照燈亮起來(lái)了,光柱里浮動(dòng)著無(wú)數(shù)細(xì)小的柳絮。而高爐此刻依舊巍然矗立,這位鋼鐵巨人在寒冬里從未停歇,此刻卻似乎也感受到了春天的氣息,它的身影在晨霧中若隱若現(xiàn),像一幅水墨畫,剛勁中帶著幾分朦朧的美感。
太陽(yáng)緩緩的升空,融化了鐵銹味的空氣,幾片早發(fā)的柳絮追著紅熱的鋼坯打旋。那些剛出膛的鋼坯躺在垛子上,通體泛著暗紅的光,倒像是被春風(fēng)醺醉了臉膛。不知哪個(gè)車間的窗臺(tái)上,養(yǎng)著盆水紅的杜鵑,花瓣落進(jìn)冷卻池,竟浮在翻涌的沸水里跳起了圓舞曲。水渣車碾過(guò)濕漉漉的廠道時(shí),后視鏡里總閃過(guò)一抹輕快的藍(lán)——那是從軋鋼廠房偷溜出來(lái)的麻雀,翅尖還沾著軋鋼機(jī)的余溫。它們掠過(guò)煉鋼新漆的除塵管道,在冷凝塔投下的巨大日晷里忽隱忽現(xiàn),最后停駐在枇杷樹(shù)上,歪頭梳理被春風(fēng)灌醉的羽毛。老張師傅摘下安全帽,任幾朵桃花歇在泛白的鬢角。他指給我看西頭那排香樟樹(shù),新抽的嫩芽映著高爐的霞光,竟比爐火還要翠上三分。下夜班的姑娘們嬉笑著走過(guò),工作服口袋里插著剛折的野薔薇,深藍(lán)色工作服的衣襟上,春天正一朵接一朵地綻放。
路邊的櫻花樹(shù)已經(jīng)鼓起了花苞,像無(wú)數(shù)個(gè)粉色的夢(mèng),等待著綻放的時(shí)刻。初春的鋼城,既有鋼鐵的堅(jiān)韌,又有春天的希望。我望著這個(gè)已經(jīng)奮戰(zhàn)了十幾年的廠區(qū),鋼鐵與春天正在譜寫一曲動(dòng)人的樂(lè)章。(漢鋼公司 楊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