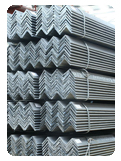難得有個回到闊別已久的陜北老家的機會,當開著車走在安塞通往城隍梁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時,除了身體,我的思緒、記憶、期盼早已飛回那個讓我牽掛無數個日夜的陜北小院。記憶里,崖畔下的窯洞,黃土夯實的墻,斜爬著的杏樹,還有那紅沙石砌成的驢圈,每一處都散落了回憶的碎片,隨著時間的遷移,這些碎片依舊能繪成讓人魂縈夢牽的畫卷,伴著我從每個清晨中醒來。
當車翻越了數十座山,行駛過最后一個沿口,到了老屋對面的山路上時,我終于看到了牽絆已久的陜北小院,在黃土與深秋枯黃的交織中,孤零零地佇立在冷冷的秋風里。玉米架,母親的大棚,父親的三輪車盡收眼底,看著是那么陌生,再看又是那么熟悉。離家不遠處的山頭上,潔白的成群結隊的山羊,圍著那山頭悠閑地徘徊著,應當是啃食著發干的秋草,院中的大黃狗當是聽到了遠處傳來汽車的轟鳴聲,汪汪地叫個不停,原本寂靜的村莊,頓時有了生機。
剛把車開進院子里停穩,等候多時的母親迫不及待拉開了車門,不由分說地“搶奪”妻子手中剛滿周歲的女兒,欣喜地說道:“哎呀,寶貝孫子,快讓奶奶親一下”,說著便在女兒稚嫩的臉蛋上親了一下。我這才注意到,母親的著裝大相徑庭,深色的條絨褲,暗棕色的皮夾克,腳上的鞋子也擦拭的很干凈,這都是母親在過年時才舍得穿的衣物,況且在塵沙飛揚的陜北,這樣的穿著每天不知道需要擦拭多少次看起來才干凈些,這也與母親曬得黢黑的臉和一絲絲花白的頭發,多少搭不上邊兒了,或許她覺著我們從漢中遠道而歸,迎接就要多少得隆重些吧。
母親在詢問我歸途是否一切安順時,我看到她的牙齒落了好幾顆,對于喜歡吃些麻花和鍋巴之類零散食品的母親來說,今后恐怕這些食物離她遠得多了些了。只是一年未見,繁重的農村生活,無形中把她催促的老了很多,饒是我無數次祈禱著歲月能停下腳步,然而,歲月卻是轉過身去,頭也不回的走向遠方,迎來了春,送走了秋,而黃土地還是那片黃土地。
不長的功夫,父親便急匆匆地趕著羊群回來了,他應該是在不遠處山頭上放羊的,看到院子里停了一輛車,知道是我們回去了,顧不得羊還在吃草,便把羊趕了回來。父親放下攔羊鏟子,高興地說:“回來就好,趕緊回屋里去,這里可比勉縣冷了不少。”說著用他那干枯的手撓了撓耳腮。我注意到父親越發稀少雪白的頭發,每一根白發,都在太陽下泛起了一道光,就像陜北深秋清晨的草地,只是稀稀拉拉地長著些草,上面還打結了寒意十足的霜層。望著一年未見的父親,我心中頓感五味雜陳,曾幾何時,父親也有著濃密的黑發,板正的身軀,但在艱辛的歲月摧殘下,剛及花甲,看上去卻已像是耄耋之年。
當父親接過母親手中的孫女時,兩張臉霎時成了最鮮明的對比,女兒臉上一塵不染,像是六月荷塘里盛開的蓮花,嬌嫩可愛,吹彈可破,父親的臉粗糙得像是瀝青鋪過的年久失修的馬路,又像是陜北那溝壑縱深干涸的黃土地。我不禁感嘆,時光會把每個人從牙牙學語的稚嫩,變成耄耋之年的殘軀,而生活無情地揚起了鞭子,加快了時光催促的腳步,而我們卻無能為力,而是默默承受著這一切。
我曾一度想把父親和母親接到勉縣生活,卻被他們拒絕了,在他們看來,樹是這個小村莊的最綠,花兒是這個小村莊的最鮮,在這一方土地上,趕著春耕秋收的腳步,喂一些雞鴨豬狗,養一些潔白溫順的山羊,生活多是愜意,又何必走進車水馬龍間,踩踏堅硬的水泥路,把自己鎖在擁擠的樓房里呢?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愛城市里的繁華,許多人為了生活,不得不背井離鄉,只能在最愛的熱土上留下了些遺憾。晚飯后與父親和母親坐在一起,聊著他們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趣事,羊啃了莊稼,狗攆了野兔,雞啄了菜園,一件件看似稀松平常的小事,在他們眼里都是樂趣,這也許就是他們總不愿意離開這個千百年不變的小村莊,清貧中守著這一方凈土的原因吧。
陜北的深秋已泛著寒冷了,漆黑的夜晚更是增添了一絲寒意,讓人忍不住裹緊了身上的衣物。屋子里,母親生好的火爐把屋子烘得異常暖和。閑聊到了來年的打算,父親說要把每只羊都養肥,就再多種些莊稼,母親說要等明年春暖花開時,多養幾頭豬,多養幾只雞,日子就有了盼頭。
隨著夜已深,父親和母親都去睡了,而我卻站在窗前,點了一支煙,透過窗,看著院中的燈有些幽暗,越過燈光,在燈的另一側,我仿佛看到了春來之時,村莊的黃土地上,杏樹和桃樹的花朵壓彎了枝頭,漫山遍野的澤蒙花,馬蘭花,父親在山坡上放羊,母親在菜園里除草施肥,就這么一年又一年,黃土地都變老了,山花卻是依舊,只是父親和母親被太陽曬得更黑了,在不知不覺中,我手中的香煙已經燃燼,燒到了的手指方才驚醒。(漢鋼公司 薛生旭)